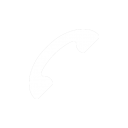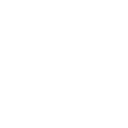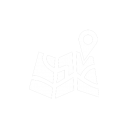寻根
我往有道的喇嘛面前,
求他指我一条明路。
只因不能回心转意,
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三百余年前创作的缠绵悱恻的情歌,穿越时空、超越民族、跨越国界,至今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传遍全球,不仅在西藏文学史享誉盛名,亦在世界诗坛声名显赫。
2015年12月16日,“先生还在身边——中央民族大学名师纪念展”校园吸睛开幕。摩肩接踵的人潮中,一些民大学子甫一得知,平常烂熟于心的仓央嘉措诗作,最初是由眼前这位被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于道泉先生首先翻译介绍给世界。1930年,他编译的藏文、汉译、英译对照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正式出版面世,这本世界上第一部采用藏文以外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专著,受到当时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
设计藏语拉丁化拼音方案、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设计藏文数码代字……作为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于道泉先生的睿智思考和深邃眼光,还体现于创建藏学专业和培养藏语人才方面。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赴北大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感情真挚、态度诚恳,促使他暗下归国决心。1949年4月,于道泉先生回国后便迫不及待与时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见面磋商,最终商定开设藏语专业和任命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并立即开始招生。由此,藏学这一专业在中国高等学府正式立足。
建国之初,为尽快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社会需求,季羡林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方法突击学习藏语。1951年6月,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云集首都组成藏语学习班。彼时,23岁的王尧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来到首都,与大家共同拜在于道泉先生门下,开始藏语学习、投身藏学研究。

大师陨落
“先生还在身边——中央民族大学名师纪念展”举办地民族博物馆,开展日随即成为校园焦点。各族师生纷至沓来,感受大师的文人风骨和精神风范。展览翌日,噩耗传来,于道泉先生弟子、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于17日18时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追忆大师情怀鼎沸校园之时,民大再度痛失“瑰宝”,微信朋友圈被悼念文章刷屏。
23日,王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虽然距离仪式开始尚有1个小时,但人们已排起长队默默等待着最后送别。“学界翘楚博古通今统摄汉藏享誉海内外,藏学宗师谨严治学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的挽联映入眼帘,灵堂两侧摆放着李克强、张高丽、温家宝、杨晶、王正伟、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等敬献的花圈与花篮,无声传达着先生在藏学领域的贡献与声望;台湾佛光山及星云大师也派代表送别王尧先生……
2013年10月10日,笔者曾跟随《光明日报》记者和现已退休的校报摄影师汤其燕叩门进入王尧先生家中采访,有幸一面之缘,每每想起往事,仍然身临其境。当年5月,王尧先生刚刚“送走”陪伴60年的夫人,些许凌乱的屋中满是悲伤味道。
“你做了一辈子西藏工作,我却一次都没有去过。”王尧先生主动提及,夫人漫不经心的只言片语,让他铭记于心。1999年,机会终于来临。中国台湾和北京大学几位学者计划去西藏自治区调研,便力邀王尧先生作为“向导”陪同。西藏之行终于变为现实,但是,“她没有福分,高原反应太强烈。”走马观花般游览了拉萨、日喀则、山南几地,王尧先生和老伴儿还没怎么体验当地风土人情便返回成都,困扰夫人多日的头疼同时一去不复返。他说自己很后悔,没给她做个体检就直接入藏,实在有些冒险。
谈起老伴儿,王尧先生仿佛总是言语间若有所思、停停顿顿。不愿再去触碰先生这份心底悲伤,记者主动将话头调转。谈及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王尧先生便开始滔滔不绝、行云流水。“尽管6月11日才开学,我那时5月份便从南京赶到北京。”他说,其实刚开始对西藏和藏学一窍不通,胸中也茫然无绪,不存在感不感兴趣的说法,只是积极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国家号召便勇往直前。
1952年,王尧与周遭同学一起离开首都前往藏区,开启了新的学习征程。贡嘎寺是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噶活佛是他们的老师,曾经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的贡噶活佛,聪慧伶俐、博学多才,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先生说自己久难忘怀。一次,他和同学们前往玉龙榭村参加一场婚礼。第一次接触藏族礼俗,热烈的场面、热闹的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刚入门不久的王尧听不明白,只能依靠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一二。“我心爱的姑娘啊,你像一只木头碗那该多好。”婚礼上的歌词让他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把姑娘比喻成月亮、鸟儿、花朵这些美好的事物,却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逐渐了解,原来藏族人民具有自己带碗的生活习惯,而且木碗会在藏袍里贴身揣着。“你想,每天贴皮靠肉般在一起,将姑娘比作木头碗是多么奇妙的构思!”
在感叹自己“无知”的同时,王尧对藏族和藏文的感情日渐升温,亦感慨于这个民族具有很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经历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王尧决定先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发掘代表性文化,这也构成他早期研究的主要内容。
60年代开始,王尧先生开始探索古代藏文发展脉络,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吐蕃时期的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三大藏文文献研究。他的藏学研究生涯始于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研习,在藏语分期和方言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译释、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轨迹、藏传佛教和藏汉佛学比勘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先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西藏文史考信集》、《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藏学零墨》等论著。王尧先生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结集于《王尧藏学研究文集》,2012年6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毕生心血描绘了一甲子的绚烂生命画卷。
王尧先生的开拓性学术贡献,让众多学者铭记于心。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对于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将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和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起到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学院沈卫荣教授认为:“王尧先生真正将西方关于藏学的学术成果引进国内,掀起藏学热,并在国际藏学和中国藏学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
1981年8月,王尧先生首次应邀赴维也纳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提交了《藏语mig(目)古读考》和《宋少帝赵显遗事》两篇论文,当他离开英语讲稿用藏语向在座学者致意三分钟时,令全场愕然而震撼。那次藏学会议,他结交了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意大利毕达克、旅美华人学者李方桂和张琨等很多国外藏学家,亦留下很多难忘回忆。1982年夏天,王尧先生应邀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席第三届国际藏学会,系统介绍了我国藏戏发展现状。1982年秋天,他应聘赴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开展教学工作……之后,他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
王尧先生当时还特别提及,欣喜于国内同行近年出国参加藏学研讨的队伍日益扩大,“这足以证明我国藏学研究的进展已是举世公认。”
寻根问祖
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著家史小说《根》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书,一时供不应求、洛阳纸贵。这本书由一明一暗两条主线组成。明线是作者经过十二年考证非洲寻根,追溯自己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从非洲西海岸被掳到北美当奴隶的悲惨命运;暗线则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惊雷乍起语境下,作者努力探求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仍然处于受压制、受排挤不平等地位的原因与根源。
寻根问祖,似乎古今中外的人们一直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虔诚追逐。王尧先生也不例外,于道泉先生和贡噶活佛,是他的“根”。
“你知道吗?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集,最早就是我的老师于道泉先生翻译传播给世界。他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是中国藏学的‘开山鼻祖’。”谈及先师,王尧先生当时话语间满满敬佩与自豪。这份浓烈而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见诸纸端。
2001年,王尧先生编著的《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集纳了季羡林先生、于若木先生和王尧先生自己对于于道泉先生的追忆文章,而且回顾了于道泉先生毕生主要学术贡献,亦通过年谱简编、纪念文章和书札选刊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先师的伟大人生。同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亦刊载了王尧先生撰写的《报国书生一片心——平凡而又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文,赞叹老先生一生的为人处事和刚正不阿。
“感谢于道泉先生,当时他以最大的耐心教导我们学习藏语。”于道泉先生不仅将从海外带回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交给王尧学习,引起他对海外藏文文献研究的兴趣。同时,他还在于道泉先生的指导与帮助下,成为中国藏学界首开研究敦煌藏文卷子的学者之一,并获得丰硕成果。
离京赴藏,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是贡嘎寺学习期间的主要任务。“贡嘎活佛是我们在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正是在他的教授下,我开始了探索藏文古典作品的第一步。”王尧先生当时回忆,1954年9月,他有幸作为助手随贡噶活佛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又协助藏学界一些大学者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五部法律文件。他说,这次经历颇为珍贵,“那些大学者的风范和学识让我终身受益。”
除了于道泉先生和贡噶活佛的教诲,还有一位西藏活佛学者对王尧先生具有重要影响。东噶·洛桑赤列是西藏东部林芝扎西曲林寺(东噶寺)第八世活佛,曾在西藏若干大寺庙和上密院学习,获得西藏最高佛学学位“格西拉让巴”,先后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及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出版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大辞典》和《西藏目录学》等著作,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开设“藏文研究班”,东噶·洛桑赤列应邀主持讲席。其间,“我承乏一些教学助理工作,朝朝暮暮与他共事前后十余年,后又一道出国参加会议。” 王尧先生评价,东噶·洛桑赤列“是西藏最为通达的大师级权威”,“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
沈卫荣、陈庆英、谢继胜、熊文彬、陈楠、储俊杰……这一串响亮的名字,是当今中外藏学研究舞台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王尧先生接受采访期间亦对他们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因为,他们都师承王尧先生。王尧先生,就是“沈卫荣们”的“根”。
其实,王尧先生并不是沈卫荣的直接导师,但他却一直对外宣称是王门弟子。“王尧先生引我登堂入室。”沈卫荣赴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博士主要研究藏学,也是由王尧先生推荐,“那些珍贵的藏学史料,也只有王尧先生家中才能见到。”
1984年9月,王尧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一门古藏文课程,许多外校学生听闻纷至沓来。虽然授课时间仅仅10个月,却改变了一些前来蹭课学生的学术人生。他们开始背离原来专业,改为研究藏学。虽然王尧先生一生没有带过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但是这些学生却一直以王门弟子自称和引以为荣,并慢慢成长为藏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王尧先生在学术上的请教和交流也从未间断。以藏学研究为中心,王门中人相互支撑、相互补给的师生情谊一直延续30余年。
对于王尧先生而言,于道泉先生和贡嘎活佛就是他的“根”;对于“沈卫荣们”而言,王尧先生就是他们的“根”。一代代民大学人,就如此这般站在先师的肩膀上,仰望星空;即便先师逝去,他们也在“根”的滋养与鞭策中,奋勇直前。
不蔓不枝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时不我待,不容半分驻足观望。时代赋予中央民族大学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任务和前进目标,只争朝夕间,民大学人和各族学子的“根”究竟在哪里?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他奠定了清华“校格”,通过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学术和教育的进步。获赞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因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四大哲人”。
被誉为总统摇篮的耶鲁大学,曾经诞生过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迄今也拥有6位总统和3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都拥有20位以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牛津大学不甘落后,25位英国首相和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熠熠生辉;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字为56……
中外历史无一例外都昭示着,大师,才是每所高等学校生生不息、方兴未艾的“根”。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创建和学术发展做出卓著贡献的大师,在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推进过程中,倾尽一生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以精深学问、开阔视野、严谨态度、高尚品格,开创了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培养模式,传承着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传统。
翦伯赞、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闻宥、于道泉、杨成志、冯家昇、陈振铎、翁独健、林耀华、费孝通、傅懋勣、陈述、马学良、王锺翰、傅乐焕、陈永龄、宋蜀华、李森……这些,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创校功臣和兴教业师。他们,才是民大积淀的厚重,历尽沧桑;他们,才是民大发展的动力,滔滔不竭;他们,才是民大坚固的根基,稳如磐石;他们,才是民大前行的明灯,不蔓不枝……
吴文藻先生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于道泉先生最先将世界海拔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的名字由藏语译成汉语介绍给世界、陈振铎先生引领中国民族音乐登上西方大雅之堂……“名师纪念展”中,师生观众依然络绎不绝。大师们治学、做人、行事的风范,令人敬仰、引人向上。
大师的胸襟与品格,不仅让师生为之动容、陷入沉思,亦惠及和鞭策着民大的建设与发展。永久性举办名师纪念展、为各位大师塑像和出版“大师学术文集”、“大师纪念文集”两套丛书……在大师期盼目光注视下,在大师精神风范感召下,在大师学术思想滋润下,中央民族大学为尝试解决“钱学森之问”,寻找特色答案。
民大正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朝着建成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目标迈进,但,绝不是独行。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