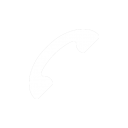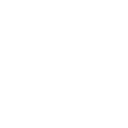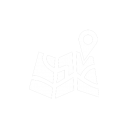郭毅生:用脚步丈量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姓名:郭毅生 籍贯:四川省自贡 民大身份: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汉城京畿大学等校兼任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尤重太平天国史。 主要著作:著作300万余言,曾参加过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的编绘工作,著有《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太平天国大辞典》、《太平天国经济史》、《罗尔纲传》、《山海集》(学术文集)、《平步留痕》(自传文集)等。
我们的采访是在郭毅生教授的家里进行的。敲开郭老的家门,他的夫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然后朝书房唤了一声“老郭,学生来采访啦!”我顺着师母的声音向书房看去,隐约能看到郭老正坐在书桌前面伏案写作。听到师母的声音,郭老脱下眼镜,慢慢起身,朝客厅走来,年事已高,依然精神矍铄。
坐在沙发上,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右手边的大书柜,把一面墙填得满满当当,我不由得走到书柜前,几乎都是太平天国史的专著。厚厚的书本整齐地排列着,还摆放了郭老一家的合照,如此温馨。我凑近书柜,闭上眼睛,能嗅到淡淡书香,还有一种,时光反复的味道。
郭毅生教授年过八旬,但仍然战斗在我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第一线,力求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可能多的都留给后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平天国史专家,但我敢说,我是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最多的学者。”郭毅生笑着说。
走一步闲棋,品一段人生
郭毅生教授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可当我提到太平天国史专家这个称谓的时候,他却说其实自己更大的贡献是在历史地理方面,包括《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他笑称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步“闲棋”。为了考证历史上许多地点的真正所在地,郭毅生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用脚步丈量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最初郭教授在接到改绘《(杨守敬标注)历代疆域政区图》(后文简称《杨图》)的任务时,完全没有准备,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有一定的地理学知识。历史地理学是兼跨文理两科,是需要考证古地名、地址和绘制古代疆域政区地图的技术性较强的学科。因此,研究历史地理学必须具备文史与考古,编图和绘图等多方面的素养,而这些都是当时的郭毅生难以胜任的。中央民族大学领导考虑到郭教授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而且他当时所在的教研室教学缺人,本不想让他转行去做《杨图》,但这时辽金元史学家即“辽史三大家“之一的傅乐焕先生特地来郭教授家中相访,并诚挚的邀请他同他共同承担东北地区历史地图的编制工作,傅乐焕诙谐地说:“在治学也如弈棋,有时走一步闲棋,可能会别开生面。”郭毅生素来尊重傅乐焕,这话也给郭毅生指点出另一番天地。郭毅生既感慨其盛情,也抱着尝试的态度,接受了《杨图》在东北地区的考证和编绘工作。于是郭毅生一头扎进了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我国边疆地区历史的归属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郭毅生说中国的考据学,要求考证名物与史事,必须内证、外证兼备。关于历史地名的今地考证,还必须落实到相对应的古城古迹和文物资料。在考证方面,傅乐焕和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同时也是郭毅生老师罗尔纲先生的著作,给他提供了范例和榜样。“我便是在这些先行者和师长们的鼓励和启迪下,走进了历史地理学的殿堂来,并且乐而忘返,成为一名老兵和战士。”郭毅生说到这里时笑了。记得一篇文章中说过,那些过程中的痛苦、心酸是属于胜利者的财富,郭毅生是一个胜利者,当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奋斗的那些日子里的喜怒哀乐的时候,眼里充满了对于那段时光的感激。
学术路上的“绊脚石”
到了文革期间,全国各地武斗正酣。在1969年的大疏散中,民族单位被迁至湖北的潜江县。这次大南迁,郭毅生必须得去,而郭夫人认为局势难料,一家人四分五裂,不如在一块有所照应,于是决意带着儿女跟随单位到湖北,于是郭毅生举家来到了湖北沙洋干校。
郭教授说他是在乡下长大的,对农村有一些情感,或者说有一种天然的爱好。来到湖北农村,他开始热衷于棉花的种植技术。于是,郭毅生开始了专心致志种棉花的淳朴生活。
直到八月初的一天,干校领导找到他谈话,通知他已调回北京,另有任用。同时调回北京的还有费孝通、吴文藻夫妇和林耀华夫妇共六名。这事在干校成了新闻。郭毅生下放一年多就“干校毕业”了,有人不服气把郭毅生调回京,因为那些“劳苦功高”的左派,才是应该提前毕业呀!而这个时候,郭毅生最舍不得的,却是这些棉花,他说棉花是他的儿女,寄托着他的希望,也凝聚着他的心血。临去,他赶去棉田里走了一趟,摘了两支新棉带回北京。1970年底,干校的赵队长来信告诉他,大田棉花亩产跨百斤,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八十斤的标准。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能想起郭老骄傲爽朗的笑声。
在20世纪60年代,郭毅生已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以前东北各国幅的编绘工作,此次匆匆将郭毅生从湖北沙洋干校抽调回京,是因为中央催着要完成此项国家任务,我校便火速组织力量,把郭毅生派遣回来应急。
从此,郭毅生与《杨图》始终相伴,从编绘地图,撰著考证说明书,参加审定此大型图集,直至它公开出版发行,其间十有余年,正是郭毅生前半生的黄金岁月。在郭毅生的著作《平步留痕》中,他把它称作是黑白山水的因缘。
耕耘在太平天国的土地上
说到郭毅生的成就,太平天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存在。
郭毅生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原因,与其说是机缘巧合,不如说是命中注定。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人民大学念研究生。说到这里,师母笑着说:“你们想象不到吧,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是分配工作的,我被分配到了中学教书,他分配到人大念研究生,这也是工作的一种,其实这样的分配也是因为他成绩比较好。”师母说到这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笑着说这也算是保研吧,师母和郭教授都笑了。
也许就是这样的分配让郭毅生从此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
郭毅生自大学时代爱好太平天国史,迄今已半个世纪有余,“兴趣鼓舞着我,问题鞭策着我。”郭老如是说。就这样,数十载的春花秋月,他多在阅读与笔耕中匆匆而过。撰著三万余言,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涉猎的领域也很广:有众说纷纭的太平天国人物评价;有关于它政权和政体性质的论证;有太平天国是否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它的经济制度与政策的问题;此外还有关于太平天国文化与艺术方面的问题。说起自己耕耘的这片土地,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开发价值的领域,我很荣幸,在这些方面略尽了绵薄之力,但愿能给后人留下些珠玑。”郭老一如既往地低调与谦逊,勤恳地耕耘。
从来中外的大史学家,都注重考察。司马迁撰《史记》曾遍历黄、淮、江、汉与华夏名都;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背负锦囊,穿行于欧、亚、非、美与大洋洲,他两度探访雅典和印度,也曾攀登过中国古长城、探访过祈年殿。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有《金田之游》和花县专访。“先师罗尔纲教授多次敦促我,要趁中年时将太平军所克名城和山川亲自踏访。”郭毅生这样说。
于是,他先后五次到广西考察和访问金田村,也曾四下江南,风雨鸡鸣寺,霜雪杭州湾;为研究太平天国所辖地区的经济状况,他住过同里镇边地水乡小店。也在常熟古寺中,细读过劫后犹存的“报恩牌坊碑”;为验证桐乡等处发现的“田凭”(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地区颁发的土地证,上记发给时间、地点、领户姓名、田亩数等,发给土地所有者或耕种者,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同时规定其遵照定制“完纳银米,不得违误”)、“易知由单”(旧时征收田赋的通知单。也称由帖、由单。单上开明田地等级、人口多少、应征款额和起交存留各项,发给纳户。始于明正德初,清代随之)等公据的真伪,他与有关学者多方采集证据;他曾亲赴大理,考察过响应太平天国号召,领导云南回民起义的兵马大元帅杜文秀的建政设施,也曾驱车黔东南,到“黄飘战役”的荒谷,看见累累白骨无人收;在鄱阳湖口,他登上石钟山,拍摄下当年石达开火焚湘军战船和曾国藩愤极投江的所在;在绍兴和金华,他对“太平天国壁画是否不许绘人物”的论断,产生了疑惑,后经反复研究,写成了《太平天国壁画人物论》,向学术界呈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一次次,用脚步丈量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郭毅生也从未忘记过太平天国史。那时的他常常去翠花胡同的科学院图书馆,读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平天国全史》等新著。稍后,台湾影印出版了湘阴曾氏所藏的《李秀成自传原稿》。这份《原稿》,被太平天国史研究者视若拱璧,他特意去定了一册。那是1963年夏的一天午前,他骑车到东城国子监附近去,将书取到手中,正待返回时,忽然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至。他急忙弃车道旁,将这本宝贵的书藏在怀里,躲进一家屋檐下。他宁愿自己浑身浇个透,也保护着这本书不被淋湿。回去后,郭毅生将影印原稿与罗尔刚著《忠王李秀成自述笺证》对照校阅,确乎收益不小。郭毅生爱书胜过爱自己,也算是一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