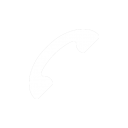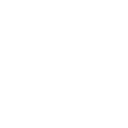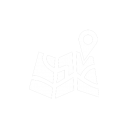现在,我每天面对自己店铺里成百上千款式的鞋子,服务购买这些鞋子成百上千的顾客。有时候我会想,这些进到我店里的鞋子就像我们考进哲学系的学生前途未卜一样,被顾客穿着去走它们千差万别的道路。有的鞋子在平坦大道上纤尘不染舒适优雅的行走;有的鞋子行走在崎岖坎坷泥泞污浊的小路;而有的鞋子一生都很少发挥走路的功能,只是偶尔从办公室走上汽车,从酒店走到办公室,然后安静的躺着舒服的休息;还有的鞋子却行色匆匆风尘仆仆昼夜不息。像《闻香识女人》一样,我养成了看鞋识人的习惯,打理这些鞋子,做好这些鞋主人的服务,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我已经满怀喜悦的热爱这些鞋子和它的主人,已经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与鞋子密不可分的生活和工作!在我1994年满怀憧憬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现在的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销售鞋子的商人。
考进民大的时候,北京各高校哲学系已被裁撤得没几个了,全北京几十所高校,保留有哲学专业的只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和中央民大四所高校,哲学褪去它神圣的光环纳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了,这可能正好应验了马克思那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经济法律生物化学等学科改造世界的功效可能更立竿见影直接有效,哲学专业的就业不再有八十年代那样需求广泛,招生数量也一减再减。我们那一届民大各个院系里,我们系的招生人数几乎是最少的,在招的哲学和宗教学两个专业里,哲学专业24个同学,宗教专业只有19个同学。但是具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是,我们这届的宗教班是建国以来国内高校培养的第一届宗教本科专业。班级的同学大多来自祖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哲学班24个同学分别来自24个不同的省,分属24个不同民族。入学报名那天,我从去火车站接我们的大巴上一下车,就听见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着热情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这首歌曲,我知道我读的是民族大学,但也没有想到全班同学没有一个的民族是相同的,一个宿舍八个同学就是八个省份八个民族的代表。由于当时哲学专业毕业就业的工作收入待遇都不如实用专业那么好,所以报考哲学宗教专业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94级全部43名同学,报考这个专业的同学居然只有一个,其余全部是通过院校调配和专业调配过来。不过,无论什么原因来到哲学系,我们都是哲学宗教学的有缘人,或许正如流行的一句佛语所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们这样的相聚,不知道前世是怎样的因缘。
哲学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小。系楼的办公面积小,系学生老师少,系内活动组织少。每天早晨,全体同学排在田径场早操的时候,我们左边是经济系,右边是中文系,全系几十人被两边上千人的系围在其中,如果迟到了想找到本系的队列,是挺不容易的事情。那时候经常做的梦就是,早操迟到了去找系的队列怎么也找不到,着急得从梦中醒来发现广播正吹着起床的号角。由于人数少,学校各类竞技活动,我们都很难取得好的名次。学校的活动,在其他系都是大家挤破头轮番淘汰才能参加,而在我们系却成了学生干部寻找参赛选手的难题。记得96年,学校传统的秋季足球联赛开赛了。我们系93级只招了读三年的专科,他们正好在96年毕业,新招的95级人数也不多且竟然没有一个踢球的人,92级的老生忙着毕业各奔东西无心联赛。全系就剩下我们94级的同学参赛!所以人数虽然凑够了但却是一只没有一个替补的球队,成绩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们的最大目标和后来2002年国家队来进世界杯后是一样的,就是能赢一场球。这个愿望在4:0输给生化系,8:0被研究生队血洗后,4:0输给朝文系后,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实力孱弱语言不通的留学生队了。我们分析留学生队来自不同的国家无法有效沟通,场上一定各自为阵没有战斗力,但就这样一只队伍,我们也被他们2:0凌辱。在学校大型活动里的憋屈,由此可想而知!到了97年秋季年赛那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鲍中同学付出一条大腿被踢骨折的代价后,才终于一洗前耻,战胜干训部队、研究生队,战平留学生队后史无前例的进入了决赛八强。据留校的同学透露,直到今年,哲学系在足球联赛的最好成绩也还是我们那一届为主力的同学创造和保持的。当时的系党支部书记李东光老师非常高兴,大大表扬了一番,带大家到魏公村的餐馆饱餐了一顿。不过在某些校内竞赛中,哲学系还是有强大实力的,学校的辩论赛,冠军和最佳辩手经常都是我们系包揽。我想这主要源于辩论赛组队要的队员不多,我们劣势不明显的原因。哈哈……
不过小有小的好处,小有小的优势,系小的最大优点就是全系的老师同学关系紧密,相处融洽,感情也比较深。2014年我们当年的辅导员宝贵珍老师到重庆开研讨会,特地找留京的同学问我电话约我见面。近二十年的分别重逢竟然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她还如当年硕士刚毕业一样充满热情和朝气,也一如年青时那般直接简单把我的生活工作情况问了个遍。记得刚入学时,她也是工作后第一次担任辅导员感觉责任重大,到宿舍把我们全班同学的家庭个人情况问了个清清楚楚,哪些同学家庭困难,哪些同学有什么思想问题,都了如指掌。北京的冬天,对我们南方去的同学是一个陌生的体验,我们都没有关窗户的习惯,结果一次降温,南方同学的宿舍里好几个都感冒了,上课缺席了大堆人。她到宿舍来探望我们,一进宿舍就感觉温度很低,伸手去探摸暖气片发现也很热,最后才发现是宿舍没有关窗户,一问我们,连晚上睡觉也没有关,就非常着急,她亲自给我们关上了窗户。晚上开班会,她在班会上做自我检讨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我们自责难过。其实,那个时候她也不过只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这一次在重庆久别重逢,不知怎么一下就想起这件事情。我已是在社会中百炼成钢的四十多岁的人,但是那一刹那,自己心里还是非常感动!非常温暖!学校有专门给贫困生发放冬季的棉衣,可是数量有限。班上的同学谁家里困难需要这些棉衣,其实她当时心里已经非常有数,不过为了让大家不至于有意见想法,她开班会让我们自己说谁困难谁需要。结果班上的同学大家都举手说需要,当时她就急了,非常生气,把大伙的自私自利狠狠批评了一顿,把棉衣给了真正需要的几位同学。直到这次见面我才告诉她当时的实情,其实大家并不是真的在抢那几件棉衣,当时大家想,如果直接让困难的同学报名说需要棉衣,这些同学可能会觉得面子上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大家商量就一起为那几个同学做掩护,最后一定是要把棉衣送到困难同学手里去的。了解了这个蒙她20几年的真相,宝老师不禁感慨万千!我问起系里老师的情况,得知张元东教授已经去世,不由得遗憾万分,难过得不能自已!张元东老师给我们讲授《天文学》,他是建国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的第一批学生,当时那一批学生很多都已经成为国内天文领域的领军人物。由于天文课的实践活动很多,仅仅课堂传授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但是系里的教学经费也非常紧张,很多实践课程都需要学生自己掏钱去补贴。张元东老师就联系他在北京天文馆,北京古观象台的同学,让他的同学帮忙让我们免费实习天文器械操作,观察天文现象。记得那一年百武慧星二号经过地球刚刚被发现,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千载难逢机会,非常想带我们班的同学去亲眼看一次彗星。但这是教学计划里没有的内容,自然就没有这笔活动经费,于是他联系在河北省兴隆天文台任台长的同学,让我们用兴隆天文台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天文望远镜观测百武慧星。可是,去兴隆天文台的食宿路费,对我们贫困山区的学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系里还担心长途远行会有安全意外事故发生,但张元东老师努力和系领导沟通保证,最后由他和宝贵珍老师两人带队去天文台实习,实习的食宿路费,没让我们学生掏一分钱,全部由他在国际期刊《自然》发表论文的稿费支付,大概是一万多人民币,在我们月生活费只需要200元的当时,那绝对是一笔巨款。我们全体同学得以在漆黑的兴隆天文台山顶,认识天上的星座,用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观测百武慧星、月亮和牛郎织女等星座的星星。兴隆天文台那次活动,几乎成为我们这个班大学经历里最奇特最美好的回忆。现在久居喧嚣都市的我,已经很少能有机会再看见满天繁星。一次我到一个乡镇去跑客户,汽车中途抛锚停靠在荒野的公路边,我一抬头,看见满天的繁星,瞬间回忆起兴隆天文台的那个夜晚,不由感动万分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天文台观测结束,经费还没有花完,张远东教授和宝贵珍老师临时建议又带我们去临近的承德避暑山庄,见习那里的藏传佛教建筑和宗教活动。我的人生如果有最美好的回忆,我想一定是这一次张元东教授捐款,由他和宝贵珍老师带队的见习考察活动。本来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去北京能去看望他老人家,给他送一双我的皮鞋,不想这个夙愿竟然永远无法实现了。在他的身上,我真切的体会到了老一批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对工作的认真,对学生无私的爱!也是他们用为人师表对我后来生活和工作的最好德育!
哲学学科深奥而严谨,也绚丽而迷人,我们渐渐沉浸在哲学的世界里。哲学系很多老师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张继选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陈亚军老师,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珍老师,讲授《形式逻辑》的李小克老师……然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教授《物理学》的杨钰老师。由于哲学发展与科学水平的密切关系,在哲学系的课程里,有很多理工类课程。我中学时就是因为理科成绩糟糕才选择读了文科,没想到躲不掉的终究会来,到了大学还得学当年学得最差的物理化学。由于没啥兴趣,也没怎么认真听课,更没有去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到了考试前,杨老师担心大家过不了,特地针对考试内容做了专门的复习讲解,悲剧的是我还是没有考过。这门课一直到毕业反复补考,我也考不过去,我成了那届学生中唯一的肄业生。离校后,自己无心去国家分配的单位工作,自己找了个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有很多时候,我经常遇见一些学生毕业后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对考试挂科科目的授课老师多数都心怀芥蒂抱着成见,但我从不附和他们的观点。我非常赞赏杨钰老师这样严谨治学的精神,在科学的领域,对与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毕业是令人遗憾的,但也给了我在哲学专业最后一个教诲,这个教诲让我在离校后的生活工作中,更努力严谨。这个经历,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激励。
四年学习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哲学本身的知识学习,也在于这些哲学老师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道德示范,还有那校园生活青春激昂的欢乐。这段宝贵的经历,帮助我把生命和心灵在世界妥当放置,让我在工作生活中少了些许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专业哲学研究工作,但在闲暇时候,我还偶尔拿起那些哲学经典来阅读,这些阅读,让我彷佛又回到了民大哲学系上学的那段快乐时光。
(本文作者,94哲学系邓世川)